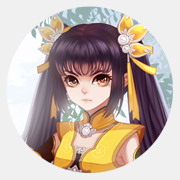“那赵将军归京一事,可要告知于韩将军?
她们二人不和,韩将军知道赵将军回京,恐不会罢休。”
就在赵普先行回京后不久,宋州节度使赵匡胤,亦大张旗鼓地回京,备好了几车的贺礼,来为新年这新旧皇权的交替朝贺。
“前次韩将军在陛下与太后面前进言……这才数月,赵将军就急匆匆等不及要回京,莫不是真的想要……”
“赵将军也是我大周的功臣,跟随先皇征战数载,立下赫赫战功。此番回来为新皇朝贺,也符合臣子礼数。
要是将其拒之门外,驻守各地的将帅们,会怎么看?
为了这一点捕风捉影的猜忌,就不许所有的将帅回京为陛下朝贺?
赵将军的心中,又会怎么想?
怪罪我们与那韩通同为一气,欺人太甚?
虽说韩将军先前在陛下与太后面前状告赵将军,但赵将军也听从旨意调任到了外地,也并未再有何出格之举。
正好,赵将军此次回京朝贺,也正好可以牵制牵制韩将军,也免韩将军做得太过了。”
大殿中,群臣屏退。宰相魏仁浦在旁听着,范质、王溥两位新宰相,商议着宋州节度使赵匡胤忽然归京的事情。
新皇继位,改换年号,各方手握大权的臣子,前来京城朝贺,是展示自己对新国君的忠臣,本无可厚非。
但恰好,后周这新一任的国君太过年幼,外敌环伺四方,朝外各地方权臣的走动必须慎重。又因为韩通的这一搅合,搞得人心惶惶,刚被韩通排挤出京城的赵匡胤,此次才过了数月就又回京,是真的来为新皇朝贺,还是有其他别的目的,身为朝内当权的宰相们,自然要好好商讨一番。
其实,在这五代十国的乱世之中,文臣武将,是不为一体的。
好听一点,可以说,是文臣主朝内,武将主伐外。
但其实谁都清楚,在乱世之中,武将在朝堂上的地位,和手中实际握有的权力,其实比一般的文臣更要大。
经过后周太祖与世宗两朝的整治,朝堂上的文武平衡尚可,地方的失衡就更甚。
文臣,落于武将一头,这是这个时代所默认的规则。
乱世之中,有兵,有力,就可称王登皇。文臣,就只是一帮陪衬的臣子,自己的官位之外,又是甚至还要担心自己的安危。
文臣们对于这些武将的了解,自然也无武将互相之间的那般熟悉。
譬如,在魏仁浦,以及范质、王溥等其他权臣的眼中,赵匡胤,就只是周世宗柴荣最为器重的将帅。
在太祖一朝,初入军旅,还无甚名号。但到了周世宗柴荣执掌天下,跟随柴荣南征北战,高平、寿州,数次大战役中扭转战局,为后周立下赫赫了战功,在军中威名大震,赵家也受到许多朝臣的亲近交好。
自然,魏仁浦、范质、王溥这些经过周世宗柴荣千挑万选坐上宰相之位的权臣,自然和赵家,以及其他的李、张二派,没有那么多的瓜葛牵连。
真说起来,比起赵家常年在外征战的赵匡胤,还不若在朝的赵匡义,要更为熟悉一些。
对于而言朝上的文臣而言,武将们的事,自己无法更无能力去管。
将帅们的权力之争,周世宗柴荣自有安排,哪怕是文臣们的顶端——宰相也不会去管。
就如在驾崩前,柴荣忽然更换的殿前司的最高统帅——殿前都点检一职,谁坐,都一样。
张永德也好,赵匡胤也罢,只要这些武将能够抵御住外敌,保住中原王朝的安危,自己的乌纱帽,就还能再在朝堂上多戴一日。
禁军是姓李、姓张、姓赵、姓韩,都不重要,自己过了今日,明日还能不能坐在这个官位上,才最重要。
而今禁军之中的将帅又起争斗,韩通与赵匡胤二人不合,朝中许多大臣都有所知晓,但韩通在新皇帝与皇太后面前状告赵匡胤有意谋反,只仅有几位宰相略知一二,也不敢过于声张。
赵匡胤如果真要谋反,对于后周年幼的新皇登基,那必是十分有威胁性的,可能造成天下大乱。
但赵匡胤是否真的会谋反,单凭韩通的一面之词,也不可能就轻易取得众位宰相的全部信任。
宰相魏仁浦对于先前韩通绕过自己与几位宰相,直接“请求”新国君与皇太后调走赵匡胤之事颇有不满,也对二人之事有所猜测。
若赵匡胤真的如此不可信任,那为何周世宗柴荣离世前,会特意让其接过张永德殿前都点检的职位?
老臣魏仁浦可是知晓,太祖郭威离世时,最担心的就是李重进、张永德二人篡权,与柴荣争夺后周的皇位。
而周世宗柴荣离开时,远调李重进镇守南方,剥夺张永德的官职,其目的,魏仁浦自是明眼相看。
赵匡胤,赵家,是周世宗柴荣培养出来制衡李、张二人的第三方势力。
可若赵匡胤真的没有不臣之心,那同样身为周世宗柴荣亲信的韩通,为何又要空口“污蔑”,周世宗柴荣将所有的兵权都交与韩通之手?
难道,韩通是周世宗又留下来制衡赵匡胤的后手么?
浸淫官场大半生,辅佐过后周两朝国君,魏仁浦对周世宗柴荣与王朴的想法还是猜到了一二。
可……似乎他们选择的这个对象——韩通,将事情闹成如此,可不好收场。
前次刚打压了赵匡胤,又准备对赵家一众下手,好在魏仁浦与李重进都将韩通劝住,慢慢对赵家下手,免得赵匡胤被逼急了反咬一口,就出大事了。
于是,这些时日,赵匡胤去了宋州,韩通也去了汴梁东边驻防,暂时离开京城消停一会儿。
或许,王朴不是与“韩瞠眼”相谋,而是告知李重进与张永德,由聪明人来办,对付赵家会简单许多。
可反过来,如果告知了李重进这些聪明人,事情也有可能会变得更麻烦,除掉了赵家,李重进与张永德再有谋反之意,也更容易。
可惜啊……
魏仁浦心中默默感慨……
就如赵普先前对赵匡胤所说的,可惜,柴荣死得太早了!留下柴宗训,还未有时间好好培养就继承皇位,太年幼了!
更可惜,王朴,比柴荣死得还早!
魏仁浦年事已高,于朝政无心无力,思想也偏保守固化,无法去干涉军中事务,比不得果决心狠的王朴。
哪怕周世宗柴荣离开了,只要王朴还在,也无需如此忧心啊……
这二人,怎都丢下后周,走得如此着急……
“罢了,赵将军既然归京朝贺,也是赵将军的一片心意。
将事情速速告知韩将军,让韩将军去处置吧。”
叹了口气,魏仁浦开口到,算是拿定了最后的主意。
没人能猜透周世宗柴荣如此布局的全部深意,但作为朝堂上的文臣们,能力有限。那些武将们不来找自己的麻烦,都要烧高香了,怎还敢擅自插手其中?
只要能维持住现今的局面,就已是竭尽所能了。
至于韩通要如何去做,赵匡胤会如何应对,他们就不再去管了。
对于这两位将帅的纷争,宰相,至少作为朝堂上文臣们的代表,所应该有的态度,要把一碗水端平。
说句难听的,就算两人中最后真的有一人夺了劝,那至少文臣们不会惹祸上身。
赵匡胤如今回京为新皇庆贺,也完全符合自己身为臣子的礼数,其与先皇交好,如此一来情面上也做到了。
不可能将其赶走,只能笑着将赵匡胤迎进汴梁了。
“那赵匡胤,真的回京了?”
“魏宰相来信,说赵将军此次回京,是以为新皇朝贺为由,不好相拒。”
很快,三位宰相的商议内容,就传到了在汴梁东面驻守的韩通的耳中。
“哼。”
冷哼一声,没有说什么,赵匡胤回到京城汴梁,已成定局。
“那李重进将军呢,可有何消息?”
“李重进将军还要坐镇淮南,路途遥远,此次,是不能回京了。
还有北方的符将军、李筠将军,都抽不开身。
只有少数节度使,会来京朝贺。”
赵普的做法,算是亲自给赵匡胤做了点播。
以为新皇朝贺的借口,纵使是那韩通,也不可能阻拦自己,否则,可是对新皇的冒犯。
而在这皇权交接的关键时刻,分别坐镇南方与北方的李重进、符彦卿等身居高职或手握重兵的将帅,可不能像赵匡胤,能够轻易回京。
京城之中,就只有韩通与赵匡胤,来一决胜负了。
“回京,速速传我军令!
无我命令,任何人,都不得擅自调动禁军!”
前次韩通与赵匡胤的初次交锋,是韩通先胜了一筹。
赵匡胤去了宋州,二人暂时相安无事。
但只要赵匡胤敢再回到京城来,那就真的是到了撕破脸的时候了。
要么离天子近,要么离禁军近,谁就握有主动权,就更有把握打压对方。
新年,这是唯一的机会,错过这一次,赵匡胤就又要回到宋州,受韩通打压了。
赵匡胤与韩通的争斗,谁胜谁负,谁生谁死,就在此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