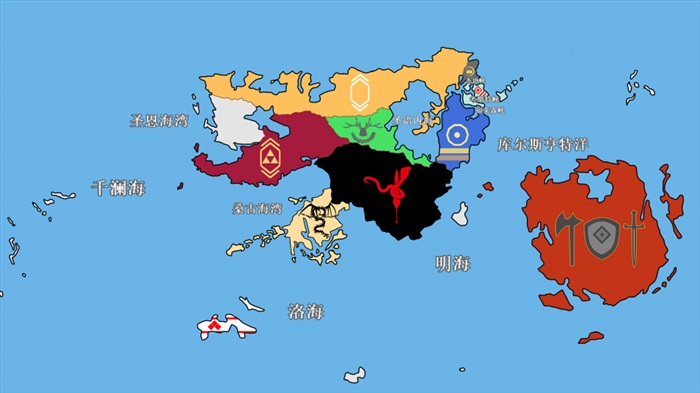“等到我醒过来的时候,发现自己身处一片陌生的海岸线上,也就是洛海之滨,”即便过去了几十年的光阴,当时发生的一切对于郎书怀来说仍历历在目,“后来我一路颠簸,来到墨轩集镇近郊,方才有幸结识了我家老太婆。”
贺君安一听,顿时愣了一下,随后连忙压着声音问道:“老先生,问一个小小问题,你知不知道一个叫生殖隔离的说法?”
老先生挑了下眉毛,咧嘴一笑,露出了两排已经发黄的牙齿:“别担心,根据我的经验来看......没啥问题。”
“您有孩子了吗?”
“有是有,就是......”话刚说到一半,郎书怀话锋一转,关切地问道,“对了,你这满身的伤究竟是怎么回事?”
“说来话长,刚才在街上看到一个臭无赖做坏事,于是就脑袋一热想出手教训他,没想到他有一大堆手下,反倒是把我暴揍了一顿,算是比较典型的见义勇为失败案例。”君安说话的时候,脸上流露出了一丝苦涩的无奈。
“胆敢光天化日当街大人......”郎书怀细细思忖了一番,“莫非那个臭无赖就是林家的少爷?”
“对对对,就是他!”
“唉,我劝你以后少招惹这种狠角色,俗话说强龙不压地头蛇,别为了逞强把自己小命给送了!”说着,郎书怀坐在病榻旁,轻轻撩开他的衣袖,察看了一下他手臂上的伤势,“这些家伙下手真狠......”
“现在好像好多了,之前连动都不能动,稍稍碰一下就疼得脑袋里一片空白。”
“我家老太婆给你诊治过了吗?”
“刚才把过脉......”
“真是太不负责任了,居然把病患撂下自己跑路,等下我一定要好好说说她!”
就在这个时候,只听见嘎吱一声,后堂的木门被推开了,“不好......”郎书怀知道情况不对,当即惊慌失措,满脸写着惊恐二字。
“你说啊!”老太太拄着拐杖,气定神闲地走了出来,身后还跟着颇有些难为情的武熙语,“死老头子,不敢说话就赶紧让开,老婆子要开药了!”
“行......”郎书怀一起身,想想不对劲又坐了下来,理直气壮地反问道,“不对,你开药为什么要我让开,我又没坐你药柜前。”
“你嫌自己不够碍眼吗?”
郎书怀急得口音都出来了:“我挺正经一老头儿我哪里碍眼了我?”
“去去去,”老太太甩了甩皱皱巴巴的麟尾,“死老头子,哪里凉快就上哪里呆着去!”
郎书怀想要在贺君安和武熙语面前展现一下自己的家庭地位,意气奋发地双手叉腰,回了一句:“我偏不!”
老太太是个狠人,厉声威胁道:“你等着,回头我给你开一副方子拌在饭里,让你吃下就睡,睡醒了正好再吃吃,永远都不会有机会碍我的眼!”
郎书怀一听,气得吹胡子瞪眼,当场拍了一下床榻:“错了错了错了,我错了。”表情十分硬气,语气却一下子软了下来,真是怂得颇有诗意了。
咚咚咚——
正在这个时候,门口传来了一阵急促的敲门声,贺君安和武熙语以为是林少东带人寻仇,心脏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而两位老人家则是对视了一下,小声嘀咕道:“他回来了吗?”
“不会,一般他回来都要先派人告诉我们......”
“臭小子,明明在一座镇子,非要住在衙门不回家。”
“死老头子,你还说,还不都是因为你......”
敲门人见医馆内没动静,越发用力地拍打木门,就好像是要拆了门板似的:“医馆内有人在吗?”
武熙语马上辨认出了他的声音:“阿爹......”
说时迟那时快,犀利的神光在武凌风眼中一掠而过,他深吸了一口气,快速握紧了双拳,关节就像是炸爆米花一样咔咔作响,随即以迅雷不及掩耳盗铃之势,照着结实的门板抬手就是一掌......一股无色无形的力量犹如狂风暴雨般席卷而过,转眼的功夫,木门就像是一块脆弱的糖糕,在众人眼前被打得支离破碎,连门闩都断成了两截。
“熙语!!!”
“阿爹——!!!”
“大叔......”
看着满地的木头渣滓,郎书怀咽了口唾沫,面部激动得微微颤动了起来:“你你你,你说砸就砸,拆迁队出身啊?”
比起惊魂未定的他,老太太倒是显得淡定自若,用一种奇怪的眼神打量着武凌风的下盘,神色颇有些凝重,好像在想什么事情似的。
“二位受惊了,我听路人说我女儿来了医馆,结果问了半天无人响应,心下担心女儿遭遇什么不测,一时心急就贸然动了手......请你放心,破损的门板我会照价赔偿,绝不会让老人家吃亏的。”
“阿婆阿公,我给你们介绍一下,这位是我家阿爹......”武熙语赶忙上前介绍道,“阿爹,君安为了保护我被别人打伤了,阿婆正在开药救治他。”
“他被打伤了?”
贺君安怕他担心,强忍着疼痛挤出一丝微笑,故作镇定地说道:“别担心,只是轻伤而已......”
“轻伤就好,”武凌风轻描淡写地关心了一句,“男子汉大丈夫,受点伤权当是历练了。”不经意间,他发现武熙语的手上见了红,两只眼睛顿时瞪得像是鸡蛋一样大,“乖女儿,你的手是怎么回事,什么时候伤到的?”
“没事的,只不过是擦破了点皮,跟君安受的伤比起来......”
“什么叫擦破了点皮,擦破皮就是天大的事情,对爹来说天都要塌了!”
“啊这......”
原来毫无掩饰的差别对待如此伤人,贺君安这下算是领教到了,家庭体验极差。
“听爹的,你回家躺着休息,千万不要多走动,我会照顾好你的!”
“阿爹,我觉得君安更需要......”
武凌风瞥了一眼贺君安,语气一下子变了,再一次轻描淡写地关心了一句:“君安,你在医馆好好休养,别到处乱走动......”
“待在医馆休养?”武熙语忍不住打断了他,“君安他......受了这么重的伤,在医馆难免劳烦阿公阿婆,不如在家休养,我也方便照顾他。”
“男子汉大丈夫,一点点皮肉伤而已,眨个眼的功夫就能好了。”
听了他的话,贺君安心里暗暗吐槽道:眨个眼的功夫就能好,你以为我是金刚狼转世灵童啊?
老太太听不下去,放下了手中的药材,咄咄逼人地斥责道:“你长没长眼睛?”
“呃......”武凌风一下子被她怼懵了。
“呐,”郎书怀耸了耸肩,“我说句公道话,贺君安是为了保护你女儿才受的伤,于情于理你都应该关心一下他的伤势,这么冷淡确实是有点过分了。”
“没事没事,”贺君安露出了随性的笑容,“大叔一直是这样的,他要是莫名其妙关心我的话,我反而会觉得不自在。”
话刚说完,武凌风微微低下了头,十分惭愧地承认道:“确实是我的问题,二老指正得非常正确,以后我一定注意自己的言行。”
“会认错就好。”说着,老太太继续掂量起了手中的药材,熟练地用臼将它们捣成药渣。
“敢问二老高姓大名?”
“免贵姓郎,名书怀,一介教书先生......”
话刚说到一半,老太太张开嘴,干脆利落地截了下来:“免贵姓邱,邱若渠。”
“您姓邱?”武凌风眉宇微微一皱,“您莫非是三针奇术邱家的子嗣......”
老太太不耐烦地点了点头:“没错。”
郎书怀一脸不敢相信地问道:“老太婆,你家这么有名气?”
“当年先代帝君寒气入体,上吐下泻数日不止,可算是急坏了不少人,帝宫中的医生都是些碌碌无为的庸才,接连诊治不见好转。”武凌风兴致勃勃地讲述起了这段故事,“无奈之下,帝君陛下只得广贴求医诏,希望天下名医可以齐聚会诊,就是这个时候,邱家的名医入了宫,不出三日,帝君体内的寒气尽除,五日之后能下地走路,七日之后气色如虹,第十天病体痊愈如初!”
“你说的那位名医就是我爹,”邱若渠满不在乎,甚至还有点厌烦,“其实你们都太抬举他了,说穿了他就是个普通的大夫,也没你们吹得那么神,只不过帝宫里的大夫都好大喜功,明明连病根都还没找到,就为了争头功乱定病因,用药自然也都偏了正道。”
“邱大夫真是谦虚了!”
“不是谦虚,我们邱家人世世代代都是普普通通的行医人,并没有什么出彩的地方,若真要说有哪里不一样的,就是邱家人行医需遵照祖制家训。”
“这个我知道!”郎书怀补充道,“邱家人当大夫除了要有丰富的医理,还需要具备三心二意,三心分别是:一颗负责到底的责任心,一颗一视同仁的医德心,一颗不断钻研的恒心。而二意分别是:一种追求药到病除的意志,一种把乐善好施的意趣,我说的没错吧?”
邱若渠点了点头,停下了手中的事情,若有所思地看向了破旧的药柜:“我爹常告诫老婆子:倘若没有这三心二意支撑,即便是拜了再高明的师傅,坐拥再响亮的名声,选择再优质名贵的药材,一切都是虚无缥缈的过眼云烟,治得好旁人却治不好自己的心。”
武凌风点头赞同道:“真是值得深思的家训......”
此时,郎书怀莫名愣了一下,随后一脸惊异地问了一句:“老太婆,既然你爹这么厉害,那我当年病怏怏的时候,怎么没见他让我药到病除?”
“其一,我爹嫌你烦,其二,你是从东华国来的,脉象之类与我们有不同之处,需要细心判断,其三,当年你体内数疫并起,犹如天煞入体,压根就像是半截身子进了棺材,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若不是我和我爹尽心诊治,恐怕你这条小命早就没了!”
郎书怀眨了眨眼睛:“我那个时候这么倒霉......”
此时,武凌风面向他,恭恭敬敬地抱拳道:“还没请教这位老先生高姓大名......”
“你这是什么破记性,前不久才介绍过,免贵姓郎,名书怀,只是一介普普通通的教书先生罢了。”
“久仰久仰。”
“你听说过我?”
武凌风愣了一下,短暂的沉默过后,露出了礼貌而不失风度的微笑:“没有,只是一般的客套话......”
“噗嗤......”贺君安没能忍住,还是笑出了声,“呵呵呵呵,哈哈哈哈哈哈哈——”
“哼,笑笑笑,笑死你算了!”
话音刚落,贺君安的笑容顿时消失,取而代之的是狰狞的表情:“疼疼疼......”
武熙语听到他的哀嚎,就像是本能反应一样快步走去,俯下身查看他的伤势:“君安,你的伤......呼——还好,没裂开。”
“姑娘,这是凌云消血散,倘若他的伤口流水较多,就将它与树液混合后涂抹在伤口之上,防止伤口出现溃烂。”老太太拄着拐杖,将包好的药递给了她,“下面这一包是天荒筋骨膏,捣烂之后将汁液煮熟,掺在湿润的泥巴里敷在淤青上,等泥巴干了淤青也就消了。”
武熙语接过了药包,颔首点头道:“谢谢阿婆,熙语一定牢记!”
“二位老人家,天色不早,我们得早些赶回天门,”武凌风毕恭毕敬地向郎书怀和邱若渠抱拳道,“这就得告辞了。”说罢,他刚一转身准备迈开步子,不料武熙语却扯住了他的衣襟,小眼神一个劲地朝着贺君安瞟。
“阿爹,君安他......”
“真拿你没办法。”武凌风清楚她是什么意思,心不甘情不愿地走到床榻旁,俯下身轻轻松松抱起了贺君安。
“疼疼疼——大叔,你扯到我伤口了!”
“臭小子,男子汉大丈夫忍着点,等回家就好了!”说着,武凌风抱着他离开了医馆,三两下就将他安置到了驴车上。
武熙语飞快上了驴车,就好像贺君安身上安装了一块磁铁,而她就是那块铁似的:“还疼吗?”
“不疼不疼,只要不动就没大碍......”
一句完整的话还没说完,脸色奇差的武凌风一屁股坐在了车前,抄起了鞭子就挥:“走!”
待他们离开后,邱若渠拄着拐杖来回踱步,神神叨叨地嘟哝着:“奇怪,太奇怪了......”
郎书怀一脸不解地问道:“怎么了?”
“她爹是个地地道道的高手,一掌就打碎了厚实的门板不说,下盘犹如磐石一般稳当,呼吸之间几乎察觉不出间隔,想必体内气劲非同凡响。”
“害,这年头江湖人一抓一大把,有什么好奇怪的?”
“他如此担心自己女儿的安危,却连一招半式都不教授于她,你觉得合乎情理吗?”
“这......”
“还有一个最大的问题......当爹的长成这个模样,真的能生出天仙一般的女儿吗?”
“啧,”郎书怀啧了下舌头,“好家伙,出问题了!”
“死老头子,你是不是察觉到了什么蹊跷的地方,说来听听?”
“不是蹊跷不蹊跷,是他忘记留下赔门的钱了,真是无妄之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