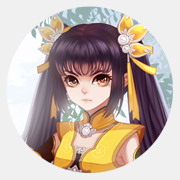关注于叙述者(旁白)这种于小说中广泛存在的概念,我先前试着写过“__故事”的四章。
但必然,对这类概念的解构势必会导致文字表意能力的下降,既然如此,我便在这里以我自己的身份略做些解释。
首先,我要进行说明的是,现在的“我”也是一种叙述者。
但叙述者又不是真正现实存在的我,这是因为想法与文字的转化过程在进行过程中与结束后势必会产生一个叙述者,这个叙述者并不真正存在或是思考,它是我于现实世界与虚构之间的一种延伸。
这一类叙述者在一个很多种叙述者构成的光谱中处于一个比较右倾的位置,因为它们几乎仅仅是复述,仅仅起到类似于传话筒的结构。
这一类叙述者的作用近似于我的笔,而并不起到描述、记叙的作用。常常出现在一部小说除序、前言、注释、后记之外的部分(通常称作“正文”的部分)中出现。
也就是说,对于前面提到的这种正在应用于本文的叙述者,它并不适于小说。
这一种叙述尚且保留了“我”的称呼,也就是说它具有一定的主体性(即使可能是虚假的)。假若我们抛弃掉这种“我”存在的意识,便是另一种叙述者了。
这一种我认为比较接近于工具书中的文字——字典等的叙述。可能这类文字看起来与叙述大相径庭,但在我看来,这依旧是一种叙述。
只不过是被剥夺了主体性以及以尽量与一种严格的框架内接近“客观陈述”为目的,但依旧是一种叙述。
接下来,我们进入可能出现于小说中的旁白的部分。
第一种,我想提到的是那类仅仅叙述,没有自我的概念,与故事和角色都不去建立联系的旁白。这也就是大多数所谓“第三人称”的小说中广泛使用的。
在我看来,这种叙述无法避免感情倾向——即便它竭力这样做——因为它的上级,也就是那个在思考并将想法转为文字的“我”无法避免感情倾向。
但我亲爱的读者朋友,假如您认为我打算在这里讲些常规的文学理论,那便错了。
我想要问您:旁白长什么样子呢?
这一类问题的答案并不重要,但只要有这种想法出现,旁白的性质就发生了无法逆转的改变。它本来的一种预设在这类问题的出现的同时崩塌,我暂且将这称为“旁白的劣化”。
但要注意的是,旁白永远也不会“劣化”,所谓的“旁白的劣化”只不过是一种假象,这也是我在《你的故事》中讨论过的。
用一种比较文学性的比喻来形容的话就是:无性之欧顿于无形中诞下婴孩,祂从未堕落,欧顿依旧无形,那婴孩是堕落本身而非欧顿的肉身。
在我们的例子(“故事”系列)中,旁白逐渐对“自我”产生认知的过程就是这种虚假的劣化的体现,再之后的故事中这种劣化愈演愈烈,最终它被取代、被毁灭。
新的、自称为“我”的“旁白”就是前面比喻中的婴孩,从它诞生的那一刻起真正的旁白就不是它了,而是高于它的某种依旧依附于写作者的事物,新的“旁白”不过是一个存在形式有些独特的角色而已。
不论如何,一部小说都需要一个叙述者,假如先前的旁白表现出来没有承当其责任的性质,那它就不是真正的叙述者,也从来没有成为过。并非其丧失了叙述者的地位,而是其刚刚才诞生,只不过诞生的过程被隐藏起来了。
有些扯远了,咱们回到有关类别上的讨论。
接下来我打算谈一谈传统的第一人称叙述。在这种叙述中,叙述者可以很明确的自称为“我”,而的确有一个对应的角色被视为这种叙述者(即便我们先前已经提到了这不可能)。至于这是如何实现的,我想这依旧是先前提到的结构的一种变体:叙述者依附于特定一个(或多个)角色并模拟其思维活动。
第一人称与第三人称都可以完成叙事嵌套,效果区别并不大,但要注意的是,即便是嵌套过后,产生了类似角色升级为叙述者的假象,但依旧,叙述者的存在是超然而不可企及的。
故而我在《叙述故事》中进行一系列嵌套过后,其中的具备(至少表面上具备)自我反思能力的主体采取不同方式企图脱离叙述本身结构的桎梏但无济于事。在这之后我们的主人公了解到了这一点,他意识到旁白本身的不可撼动,于是于《你的故事》与《我是故事》之间采取了另外的措施:用诡计叙事的方法取代了被完全“劣化”为一个主体的旁白。(虽然这于理论上无法实现,但是,做出评价的永远都是读者,故而能够欺骗读者使其相信某件事就可以等同于能够做到它。)
在《我是故事》的最后,结构性本身的化身(那个后引号)还是找上了已经将自己变成叙述者的我们的主人公,但不论如何他也已经结束了整个故事,因而其也没有了价值。
有些扯远了,但其实也没有,因为这就是我想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