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是十一月十一号,喻涌像往常一样被六点半的闹铃唤醒,来到卫生间准备洗漱。洗手台上面摆着一面椭圆形的镜子,镜子有着光洁的银色表面,却在边缘处染上了不知从何而来的暗褐色斑点。他在第二个抽屉中找到牙膏,右手两指按住牙膏底部,小心地挤了一点到牙刷上,这一系列的动作他完成得很快,仿佛他已经将它们重复了无数遍一样——为什么要说“仿佛“呢?这就是他的生活,他也的确将这些动作重复了无数遍才对——不管怎样,挤好牙膏后,他开始对着镜子漱口,可当他抬头看向镜中的时候,那里出现的却不是自己那张熟悉又令人厌烦的脸,取而代之的是一张少女的面庞。
那少女的五官完全不符合人体的构造,却能给人带来强烈的审美冲击,那奇异的阴影、透视、比例,粗看之下是混合了多种审美风格的极端精致,可一旦细看,你会发现她既像真人又不像真人,既像CG又不像CG,既像插画又不像插画......那诡异的混搭感仿佛带人来到了致幻剂吸食者眼中的世界,所有的感官都像受热的毛孔一样张开,所有静态的事物都开始旋转运动,那少女的脸仿佛不是一张脸,而是一个漩涡,一个不断向外抛掷着美感符号的漩涡。
我们会用花朵、画作,乃至太阳和星星来比喻一个人的美貌,但这些比喻通通不能用在她的身上,原因很简单——她美得不像任何东西。当喻涌将视线从那张脸上离开,在卫生间内四下扫视时,他吓了一跳,那些平日熟悉的事物在他眼中突然变得诡异与恐怖——那是恐怖谷效应,当你见过真实的模样后,再去看那些仿制的赝品,它们那虚伪的美感就会立刻被识别为恐怖与不协。
看过镜中少女的“美貌”后,就好像意识到整个现实都是那少女的赝品一般,喻涌眼中的世界一下子坠入了恐怖谷。
喻涌难以置信地睁大了眼,镜中少女和他同步露出惊讶的表情。他连忙伸手往双颊摸去,镜中的少女用纤细的双手挤压着脸颊,可爱地嘟起了嘴,用手在脸上连抓了几把后,少女的脸上突然露出了复杂的神色。
喻涌确信,自己的脸摸起来和平常没有任何不同,无论是脸型,大小,还是粗糙程度都符合他应有的身份——一个二十七岁的健康男性,他甚至还在嘴角摸到了扎手的胡茬。
他看着镜中的少女,镜中的少女看着他,两人眼中的迷惑别无二致。
看到放在洗手台上的手机,喻涌突然有了主意,他打开手机,调出前置摄像头。摄像头将接收的光学信号投射到屏幕上,果不其然,屏幕中他的模样没有变化,依然是该长怎样长怎样。
再次看向镜子,镜中的少女嘴角带着微笑。她对着他挥了挥手,而他的双手根本没有做出任何动作。
喻涌看着少女的眼睛,那双眼睛一会是茶色虹膜与黑色瞳孔,一会是金色虹膜与红色瞳孔,它们不断闪烁着,在两种色彩间快速地来回切换。他试着闭上眼睛再睁开,可睁眼时那少女仍在镜中,她不是梦幻,因此任凭他再努力也无法驱除。于是他决定暂时不去管这个奇怪的幻觉,他刷完牙,用冷水洗了脸,然后无视镜中少女和她的微笑,径直离开了卫生间。
可还没等他走出门槛,正对着卫生间门口的那面巨大落地镜又给他吓了一跳。
那位少女在镜中看着他,涂着颜色诡异的指甲油的十指在胸前交叉,她穿着一身纯黑的宫廷风格装束,那装束大体上可以归为哥特洛丽塔的一种,但是在细节的设计上几乎同少女的面孔一样奇诡怪异,不属于这世界上的任何一个流派,乃至于远远地脱离了人间的范畴。
这面镜子一开始就在这里吗?惊吓之中,喻涌的脑中突然闪过这个念头。可还没等他进一步思考,少女就开口说话了。
“那些人的命比蝼蚁还贱,活着也只是徒增痛苦,现在死了正是好事一桩,你哭个什么劲呢?”少女说着踢了踢脚边的一滩肉块,金红交加的眸子扑闪着,溅在脸上的殷红液滴衬得她的嗤笑愈发瘆人。除了摊在脚边的碎尸之外,房间里还摆着好几具尸体,一个中年男性的上半身面朝下趴在地上,他的部分肋骨与脏器膜暴露在外,像是遭到了鬣狗的啃食;一对男女被挂在天花板上,他们的腹腔张开,里面没有任何脏器,他们的脚下都放了一个用于盛装鲜血的塑料桶;少女身后的墙上固定着一个幼童的头颅,幼童两只稚嫩的手被从肘部切开,摆出剪刀手在头颅下面交叉,像是壁炉上挂着的某种猎物标本。而在门边还倒着一个年轻女性的无头尸体,她是死得最为干脆的一个。
“怎么样?”见他看得目不转睛,少女露出了一种看到绝世艺术品的迷狂眼神,“我的摆盘技术还不错吧?”
“是不错。”,看着白瓷盘子里呈现出精致立体结构的巧克力蛋糕,他随口夸了一句。
“又走神了?在想什么呢。”少女明显听出了他语气中的随意,微微皱起了眉。
“没事,想到了一些以前的事情。” 他抱歉地笑笑,抬起头与少女对视,少女淡茶色的虹膜清澈如同湖水,纯黑的瞳孔没入其中,像湖底的空洞。
即使今天不是工作日,他依然在吃过早饭后出了门,少女在身后问他去哪,他没有回答。
他两手空空地来到公寓楼后方的垃圾场,这里停着几只乌鸦,它们收紧翅膀,站在地面或垃圾箱的边缘上,深红色的眼珠一眨不眨地望着同一个方向。他想起前两天房东拜托他把“那些垃圾场里的乌鸦”赶走,应该就是在指它们。
“我不会把它们赶走的。”他说。说完,他两手空空地离开了垃圾场,走向位于相反方向的公交站。
公交站里空无一人,即使对于休息日,它也冷清得过头了。他等了半个小时,没有看到一辆车。于是他才想起来这个公交站已经停运三个月了,他有些焦躁,因为最近的可用公交站在三公里外,从这里出发至少有三十分钟的路程,错过时间的风险压迫着他,他开始后悔今天没有提前出门。
走在前往公交站的路上,他看见道路两旁的景色发生了一些奇异而美好的变化,两排房子中间是一块长方形的空地,有几辆大货车停在那里,像几口巨大的棺材。车上堆满了货物,高高地垒了起来,用黑布盖住,也不知道装了什么。月亮在这些货车上投下严厉的目光,他的影子在身后投下一个扭曲的心形。
他看了一下表,决定不回家,而是直接去看望■■■,一辆轿车在他身边停下,一个衣着华丽的男人跳下了车,一道箭形的金色光斑在他镫亮的鞋面闪烁,几个没有干涸的小水坑,反射着黄昏时分的阳光,像柏油路上几道古怪的伤痕。他看到道路两旁的拱廊呈现出令人愉悦的弧形曲线,排成一排的天使石雕抱着手中无弦的竖琴。他感觉自己正沉浸在幸福的氛围之中,黄昏的空气透澈而清新,这让他有些头晕。
我多么幸福。他想,周围的一切都在盛赞他的幸福。
他坐在公交车上,温情地注视着身边的每一个乘客,他们的行为相较于平日并无任何区别,却也因为他的心境而染上了一层美好的滤镜。
不一会儿我就能看见■■■了,他想。她会在门口迎接我。她会说她简直都等不到晚上了。
他突然愣了一下,原来自己已经坐过了站,没有在应该下车的地方下去,他往车门走去,被一个胖男人的脚绊了一下,那个男人正在看一本医学杂志,面对他的道歉,胖男人连头也没抬,只是冷冷地,生气地哼了一声,将腿收回座位底下。
他又不好意思地笑了笑,走到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打开的车门前,双手紧紧抓住铁扶手,准备跳下车去。底下,柏油路飞快地闪过。他飞快地往下一跳,脚掌上立刻传来难以置信的压力,两条腿控制不住,自己跑了起来。这时,一件奇怪的事发生了,他听见司机的一声怒吼,整辆公交车猛地倾斜过来,只差一点点就从他身上碾了过去。他吓出一身冷汗,好似一道惊雷划过全身,然后,他一个人静静地站在闪亮的柏油马路上,他四下望望,到处都是他自己的身影。他望着前面的一个后脑勺,他原本以为这是其他人的,过了一会儿才反应过来那是他自己的,他追上自己,感觉整个人都在震动,好像一根鸣响的音叉。
他全身上下都很疼,又回到了那片空地上,他认出了远处的那几辆大货车,不由得笑起来。车还停在那边,活像几口大棺材。车里头到底藏了些什么呢?珍宝?巨兽的骨头?或是堆积如山的豪华家具? 我必须去看看。要不然■■■问起来,我还不知道呢。 他匆匆推开其中一辆车的车门,进去一看,空的,什么也没有,只有一把草扎的小椅子,椅腿少了一条,歪歪斜斜地立在车中央,样子很可笑。
他耸耸肩,从货车的另一边出来。眼前又涌来火红的晚霞。这时他面前是那道熟悉的长廊,再往前去就是■■■家的窗户,窗上插着一根绿枝。■■■亲自打开了门,站在那边等他。
他不声不响地笑着,跑过去拥抱她。把脸紧贴在她温暖的黑绸衣上。
她打开门,他发现自己马上进了餐厅。餐厅非常宽敞明亮,这让他十分诧异。
餐厅里,餐桌上铺着雪白的桌布,周围坐着一大帮人,很多人他以前从没见过。他在其中找到了刚才在公交车上看杂志的那位胖男人,这会儿还在嘟嘟囔囔。
他略带尴尬地点头招呼大家,在■■■身边坐下。就在此时,他突然全身一阵剧痛,和前不久经历的那次疼痛一模一样。■■■的黑色绸裙飘荡远去,消失了,最后变成了颜色不详的灯罩。他躺在灯下,难以想象的疼痛挤进身体,除了那盏摇摆的灯外,什么都看不见。他的肋骨压迫着心脏,压得他透不过气。有人从后面使劲扯他的腿,眼看就要扯断了。不知怎的,他挣开身子,灯闪出了绿色的光,他发现自己和■■■稍稍坐开了一点。他刚看见■■■华丽的黑色裙子,■■■便笑起来,笑得前仰后合。
他觉得要赶紧说说刚才发生的事情,于是冲着所有在座的人——包括那位气呼呼的胖男人——挣扎着说道:“我家的楼梯间很奇怪,它白天的时候看上去很正常,但一到了晚上......”
他觉得他已经把一切都说清楚了,大家显然也都听明白了……■■■低低地笑了笑,说道:“没关系,会好起来的……”
他开始觉得累,想睡觉。他看着■■■黑色的华裙,想伸手去抓,可这时疼痛又一次发作,他眼前的一切又清晰起来。
喻涌呆滞地躺在床上,插着呼吸管,奄奄一息,灯不再摇摆。那位熟悉的胖男人现在变成了身穿白大褂的医生,正在察看他的瞳孔,小声地说着焦急担心的话。好痛啊!……他的心脏跳动得越来越艰难,眼看就要爆炸了……这太荒唐了。■■■为什么不在这儿呢?
医生咂咂嘴,皱皱眉头。
他周围的一切都暗淡下去,只剩下光秃秃的死亡景象——居民楼圆筒形的楼梯间,在黑红色的夜幕中看起来像一只有着黑色瞳孔的眼睛,除此之外,它还与另外一个什么东西相似,是什么呢——他不记得了。这时,他想起一件事,就在今天早上,或是更早之前的什么时候,有人问过他一句什么,她问的是什么呢,好像是关于他要去哪的问题,是的,她确实问了他要去哪,但是除此之外,她还问了一句别的什么。他无论如何都想不起那是什么——他想啊想,忘记了那不断向他压迫而来的深渊。
“你还好吧?”
“好好好号灏號呺侴㞻獔??!”
他看见自己躺在草原的中央,月亮在他看不见的地方撒下光亮,少女压在他的身上,看着他的瞳孔不断地一张一缩,他看着少女的眼睛,那是一双有着黑色瞳孔的眼睛。他看见少女的嘴正不断地一张一合,他听见。
“怎么回事,这是怎么回事啊?”
他不解地喊着,看着被自己压在身下的男人,他的脸怎么那么熟悉?
他。
今天是十一月十一日,■■■像往常一样在六点半醒来,来到卫生间的镜子前准备洗漱,可当她抬头看向镜中的时候,那里出现的却不是自己的脸,取而代之的是一个陌生男人的面庞。
......
今天是十一月十一日,■■像往常一样在六点半醒来,来到卫生间的镜子前准备洗漱,可当■抬头看向镜中的时候,那里出现的却不是自己的脸,取而代之的是一个令人感到熟悉的后脑勺。
......
今天是十一月十一日,喻蛹像往常一样在六点半醒来,来到卫生间的镜子前准备洗漱,可当抬头看向镜中的时候,那里出现的却不是的脸,取而代之的是。
......
“那件事已经不会发生了。”
“那件事不会发生了,因为它已经发生过了。”
他看着桌子对面的那位少女,努力想理解她话语中的含义。
医生对他说,它很饿。
但是他不饿,即使餐盘里摆着的是美味的三分熟的人类内脏。
“不对,你再仔细看看,餐盘里面摆着的到底是什么?”他看着桌子对面的男人眼中的景象,出言纠正道。
他眨了眨眼睛,餐盘里摆着造型精致的巧克力蛋糕。
他叹了口气,对着对面的少女说:
“我和你的相性实在是太差了,”少女顿了顿,接着说道,“我没想到仪式本身也没能完全逃过它的影响,仪式本来应该在非敏感群体中随机选取一名目标,可它现在似乎只能选到那些最危险的群体......就像你一样。”
“你在说什么?”他疑惑地问道,深渊又开始在他的眼中旋转起来。
“我不能告诉你太多,一旦接收到了某些信息,你的主体性就会完全崩溃,那样的话我们就必须从头来过了。”
“我只能告诉你最简单的信息,首先......”少女停下来,观察着他神色的变化,“首先,你已经死了,还记得死是什么吗?”
他想说不知道,但是一晃神间突然又看到了那黑红色的,旋转着的深渊——那是少女的眼睛。于是他开口说:“还记得。”
“然后,你之所以会死,是因为你被吃掉了。”
“被吃掉了......”他愣愣地盯着餐盘里的巧克力蛋糕,对于什么是“被吃掉”,他的理解要比什么是“死”更加深刻。
少女微微颔首,接着说:“它之所以要吃掉你,不是因为它想吃你,只是因为它太饿了,对它来说,吃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有东西吃。”
“除了你之外,它也吃掉了其他很多东西,它在你们当中挑选一部分人吃掉,但对于我们,它几乎吃掉了全部。”
他摇了摇头。
少女指向餐盘中的蛋糕,“对于你们,它只是嗅了嗅蛋糕的气味,而对于我们,它已经快把盘子都吃了。”
他不再说话,也不再动作,似乎陷入了沉思。
少女仔细看着他的眼神,那其中似乎恢复了几分清明。
“我们之中有一些人,在被吃掉之前找到了各种方法,想要让它把吃掉的东西吐出来,或者阻止它继续吃掉剩下的东西,或者让它吃得稍微慢一点。”
“我就是那些方法中的一个,”少女说着,她的身影逐渐变得清晰,“我的身体是它唯一不能马上吃掉的东西,只要灵魂还完好,就能一直坚持下去。”
“灵魂是一种非身体的容器,它的作用是在超越身体的地方容纳主体性,它被创造出来的目的就是配合我的能力。”
“灵魂是远比身体强大的容器,但在它面前依旧足够脆弱。我是第一个容器,在很长很长的时间里,我渐渐变成了那不是任何东西的东西,现在已经到了最后一刻,我必须离开,而制造我的人不允许容器就这么消失,他们留下了一个捕虫网,用于抓住那些失去身体的灵魂,把它们塞进这个身体里,让它们接替我,继续发挥容器的功能。”
“它是什么?”桌子对面的男人抬起头,重新与她对视。
“它是吃东西的人。”少女张了张嘴,却是没有继续说下去。
“我可以走吗?”男人又说。
“我正要说这个,我离开的时候会留下一个豁口,你只要找到那个豁口,然后跳进去就可以走了。”少女接过他的话,“我们阻止不了它,无论我容纳多少,它都会有更多,连减缓它的速度都是不可能的。最后的结论是有没有我都一样,因此你没有必要留下来受无意义的苦。”
“我已经死了,能走到哪里去?”
“到你应该去的地方,也许是天堂,也许是一个没有灵魂的现实,也许是另一个世界,也许是在你的世界开启一段新的人生,无论如何,都远好过继续待在这里。”少女说着,从椅子上站了起来,“我们现在来试试看你能不能抓住豁口。”
他又看到了那个黑,紫,红三色交杂的漩涡,比之前的任何一次都要清晰,它无言地旋转着,其中吹起的冷风落到身上,让他微微战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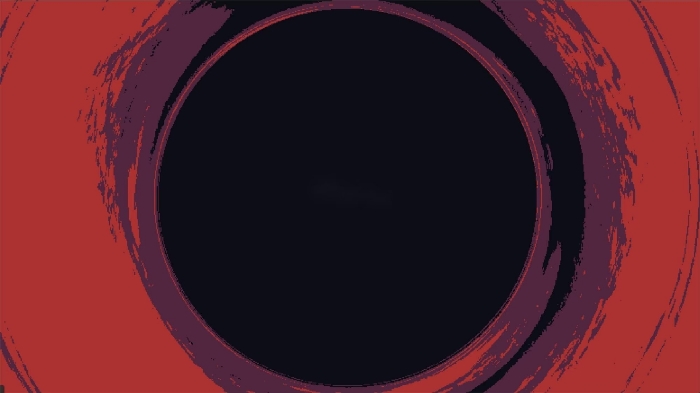
我要从这里跳下去吗?
它看起来很可怕。
“我能相信你吗?”他的声音意料之外的平静。
“如果你不相信我,你还能相信谁呢?”少女坐回椅子上,她的面前是摆着餐盘的餐桌,她的身后就是窗户,窗外一片漆黑,是晚上了吗?
“你眼中的豁口是怎么样的呢?它令你如此恐惧。”少女拿起餐叉,并不进食,只是把餐叉竖着抓在手中。
他没有回答,红黑紫三色的深渊旋转着,旋转着。
“我是因为癌症死的。”他说
少女没有回答。
“我不想再活一次,能把我送去别的地方吗?”
少女摇了摇头:“我不能向你保证任何东西,我知道它不会放过任何一个角落,即使是死亡。”
“它到底是什么呢?”他说着,眼前出现了一片熟悉的阴影,它涌动着无规则的丑陋身躯,所有的边界在灰黑色的雾霭中渐渐消泯。
少女拿着餐叉,在她身后,窗外一望无际的黑夜里突然燃起了火苗。
“你看过《蜡烛湾》吗?”
“在这部木偶动画中,一些具有典型性的场景被不断重复,Janice在她幻想的冒险旅途中一直在哭,但她开启这场冒险的原因却是为了逃避无聊的现实;Percy是个懦弱的海盗,他的身体由‘尸块’拼凑而成,这隐喻了他的某些人格特质;至于Laughingstock,它总是推动剧情的那一个,如果没有它,整部动画只会剩下哭个不停的小女孩和神经质的木偶人。我们现在来到了深渊面前,Percy又开始展现他令人厌恶的踌躇不决,Janice眼看着又要进行她新一轮的哭泣表演,就在这时,拥有永不合拢的巨口的Laughingstock说话了,它说:‘你必须去,你必须现在就去。’ ”
火焰在漆黑一片的夜中燃烧,被锈蚀的窗框在了房屋之外,少女一手拿着餐叉,她面前放着盛满的餐盘。
“我必须现在就走,每多待一秒,就多一秒的风险,注意看着那道豁口。另外,如果你不打算离开,一定要记住下面的话:‘把痛苦转移到身体上,不要让它们停留在灵魂中’ 。”
那道深渊再次升起,几乎吞没了他的整个视线,可是这一次他还看到了更多的东西,他看到深渊变得透明,露出了其后的景象——被火包裹的景象,少女拿着餐叉,端坐在椅子上,她穿着黑色的T恤,餐盘里盛满了白色的食物。
“不要看。这里什么也没有。”
少女又重复了一遍
“这里什么也没有。”,然后,她猛地扑倒在餐桌上,脑袋直接砸进了餐盘里,白色的食物四下飞溅。
他愣愣地看着这一切,深渊在他眼前逐渐淡去,他吓了一跳,以为它就要消失了,但它只是变得更淡,最后成为了他视野的背景。
他突然发现自己什么也看不到了,脸上传来冰凉黏腻的触感,他猛地抬起头,发现自己刚刚是把脸砸进餐盘里了,可是那餐盘里装着的不是什么食物,而是一条条黄白色的肥硕蛆虫,它们还在蠕动,即使其中一只已经被砸成两段挂在她的嘴角,它依然在蠕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