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已经知道除了这个时代的精神之外,仍有另外一种精神在起作用,也就是说,是它在统治一切深度
——卡尔·荣格
昨天晚上我下到南森桥的时候,有个男人一直在站在光谱酒吧的镭射灯下面,我一开始觉得他在等人,但这样的话他的站位就太奇怪了——他站在门头靠墙的角落,镭射灯的背光处,与其说在等人,不如说像在躲着什么人。我回来的时候特意往那边看了一眼,他还在那里,姿势一点都没变,我惊讶极了,忍不住凑上去确认那会不会只是个像人的影子。
“然后呢?”梓没有看我,一手托着腮,另一只手拨弄着桌上的钢笔。在不了解她的人看来,这显然是心不在焉的表现。
“我怀疑他看到我了,那个时候我们的距离近到能看见对方瞳孔里的反光——我回家之后一直在想,何至于如此呢,一个人到底要在这一天里经历什么,才会导致他在酒吧门前背光的角落里一动不动地站上好几个小时呢?”
“啊,所以那确实是个人咯。”梓口齿不清地嘟囔着,半个脑袋都埋到了臂弯里。
“今天早上出门的时候我想到了,他是在需要着某些东西吧,一个人有需要某些东西的迹象时,是无论如何都藏不住的,总能从外面一眼就看见。”我故意放缓了语速,确保最后一句话能衔接上预备铃声,梓还是那副百无聊赖的样子,好像怎么坐都不舒服似的。她的表演能骗过很多人,但是无论被骗过的人组成了多么硕大无朋的群体,我总不会是其中的一员。
那么,为了一个捕风捉影的流言,你会做到什么程度呢?
梓突然抬起头掠了我一眼,是察觉到我的想法了么?她的眼神藏在那对紫红色的视器官后面,即使是我也无法看穿。我从来无法解读她,或她们这些人的眼神,将来也不会能做到。不过没关系,我并不需要这种能力。她的瞳孔锁定了我,在我的大脑中挖掘了一阵后兴致缺缺地转开了,我的确信再次得到佐证——我对她来说并无价值。
上课铃一响,原本趴在我桌面上的梓一下子就转回了端正的坐姿,我把她留下的钢笔收好,准备下节课间还给她。
“同学,请出示学生证明。”这时,清账委员刚好走到梓的座位旁。
梓上半身几乎不动,只是抖了抖右手腕,让一颗12.7x99毫米的红头弹从袖口落到桌面上,清账人捏起来看了一眼,然后重新将它摆回课桌的一角。从这个角度看不见梓的表情,在我的想象中,她又取回了那种沉静的,仿佛在等待着某种东西的神色。
“到你了,同学。”清账人白皙的指节在我的桌边敲响。
我犹豫了片刻,说是片刻,在不同人的眼中也会有所不同。对梓而言,这个时间实在太久了,久到每个瞬间都有可能让她猝然转头看向我——以我这种人绝对无法分辨的速度。
我犹豫了片刻,将那张卡片递给清账委员。那是一张纯白的闪卡,从中央偏右处起始,黑色的曼德勃集伸展着它崎岖而无限精细的形体,占据了三分之一的卡面。
清账人接过卡片,那东西在她的手上停留了一些时间——比.50停留的时间久得多——然后重新回到我的手中。
“下一个......”清账人走过我身边,声音变得遥远,仿佛在一瞬之间便与我相距百尺。
梓的身子端得很直,她紧收着翼状的肩胛骨,让颈椎与脊柱连成平滑的弧线,白色校服贴在背部的凹陷处。在阳光灿烂的日子里,组成校服的白色织物会在光照下变得略微透明,那时候,你就能隐约瞧见隐藏在校服之下的更为厚重的东西。我眯起眼,被白色织物上的一个细小污点所吸引,清账人的问话已经停了好一阵,在我身后很远的地方传来混合着拖拽与击打的声音。
梓下颌处的肌肉无法抑制地抽动起来,我透过她垂到肩头的碎发,想象着此刻她脸上露出的狰狞笑容。
再次经过光谱酒吧的时候,我没有再凑近去看那个男人,而当我在桥头的检查口向后回望时,那个身影几乎已经不可见,只有还未彻底消失的印象在他原本应在的晦暗之处留下一个同样晦暗的污点,他一定是在躲着什么人吧,我试图在想象中看见他的眼睛,那应该是一双迫切的眼睛,一种不可隐藏的需要从他黑洞洞的一对瞳孔中满溢出来。
而且,那天晚上,我居住的街区的所有大门都半掩着。
我一直在用余光观察着邻座上那人的举动,即使是在说话时也同样。不知道什么时候,他们凑到我的近前,遮住了笼罩在所有人头上的冷白色灯光。
“可是小餍,你会开车吗?”
我试图在他们的面貌上寻找痕迹,血红的痕迹,内外翻转的痕迹或蠕虫的痕迹,人们开始转过身,用垂下长长黑发的头颅面对我,时间逼迫着我迅速做出权衡。
“不......”却只是嗫嚅着说出了“不”,我曾经突然想起来这并不是我真正做出回答的那个问题。
于是,人们哄笑着从高台上伸出长着黑色长发的头颅,鞠着躬,雨一般落在我的身边。
为了躲避不断发动的美化委员会,我们来到学校的体育馆,已经在这里待了五天。
每天晚上,场馆里的灯光都会有两小时变为红色,每到这个时候,人们就会收拾起狂欢的遗迹,四处躲藏。所有的出口都被看守之墙挤满,红色的灯光会迅速将塑胶地面侵蚀成红色,这样在我们的末日到来之后,飞溅的红色液滴将永远不会被呈现在体育馆翻转的绿幕上。
我看向梓的眼睛,那对狡黠到近乎发光的紫色竖瞳从未像如今这般盈满笑意,她将枪口抵在地上,正试图将一具没有头颅的血红残躯从绞机中拽出。
锈红色的巨大阴影在梓身后随着灯光的明灭而起落,时不时将她少女形状的纤细阴影遮盖,那是看守之墙的一种延伸——梓的私人财产。
为何已经是不可见的东西,却还要在灯光下投下影子呢?梓的目光五次扫过我的面孔,我没有对上她的眼神。
“一定要这么做吗?”
“一不一定的......其实也不一定吧,”梓说着,朝着空中打了个响指,“只是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咯。”
“不过,”她突然用手指在我鼻尖上刮过,移动的轨迹同时从我的枕叶中抹去,“不管怎么说,你都不构成呢,真是可惜。”
“你认为你们比他们更好吗?”
“他们?你说那些‘吱吱’吗?”这个问题似乎牵制住了梓,也许她只是借着这个由头稍作歇息,无论如何,在我的眼睛看来,她正静止着陷入沉思。
【我的脑袋里有一只吱吱作响的虫子】
“我真希望我死了,可是我做什么都摆脱不了它,邻居们都喂了虫子,但我找不到我的家人了——唉,可虫子还在吱吱叫~”梓戏谑地哼唱起来,“这些东西和我有什么关系,嗯?”
“你挖空他们的脑袋,那里面真有虫子吗?”
我走出刑房的时候,看到转角处蹲着那个红色的东西,我疑惑地看着它,就像我只是在看着一个神圣物体的时隔共振成像。
她校服下的作战背心到底是用来防护什么的呢?那东西连步枪弹都能挡下来,可学校里只有她们有枪,难道是用来提防自己人的吗,可是她们从来不会相互杀戮。
她们走后,人们纷纷从自己的角落中离开,打开内部反锁的大门让清洁车队进来。这是一种象征性的躲避,同时也一举两得地以躲猫猫的形式娱乐了她们。
你是否经历过那个时刻,从你儿时起就开始期待的时刻,你待在它的关隘前就仿佛看到所有可能的选择和现实都混在一起。
美化委员们不会让你没有事情做。
那个人顶着层层叠叠的高帽子走上讲台,暗红的浸渍从它们尖锐带角的边缘盘旋向上,汇集成一种即将滴落的粘稠。那是一座染血的织物的废墟。
你认为你能杀死他们所有人吗?铁锈说,这是不可能的,影像的速度永远比现实的速度快得多,你看看这里,多么宽敞,多么昏暗......
于是少女手中的美工刀出鞘又收回,人们排列得多么整齐,她想,我会用最快的速度冲向他们,如果运气好的话,在任何人反应过来之前我就能割断他们其中一个的喉咙。沉浸在这样的想法中,少女把握住刀的手指捏成了青白色。
即使这样也不行,一个,或者一个也没有......即使杀掉一两个又能怎样,人们排列得多么整齐,这些金属的终极又是多么疯狂而悲凉啊,它们难道早就能知道么?
色彩斑驳的锈迹爬满了刀片表面,红色,黄色,褐色,黑色,一座森林在黑色的斑点上生长。穿着西装的男人留下一个背影,带着她们向海底走去,她突然害怕了,很奇怪地,她不知道自己在害怕什么。这是一种古老的家族遗传疾病,涉及一种或多种无法溯因的非器质性恐惧症状,当人们走在阳光明媚的大路上,他们为什么会突然蹲在地上掩面哭泣呢?少女是世界上唯一研究这种疾病的专家,在过去的十五年里,尤其是童年在家族刑房中度过的那段时间,她一直试图为这种疾病命名:辛辛那特斯综合症、光影幻界斯洛普(Shadow-Lights Sloop)、再预见性熟异感障碍、反-人类世解域性自物化,这些名字被历史性地遗忘之后,她开始用“现实恐惧症”来称呼它们。我想起一场关于影子的演讲,坐在第一排上倒悬的观众们目击了舞台本身增殖-分裂的物(Thing)之真相。
如果拿着枪,我就能杀掉所有人。她自我安慰地想,但是,在她目击的那些画面中,没有一种起舞的黑暗真正追上了每一个在夏日中窜逃的生命。我需要更多的力量,她又想。怎么样的力量呢?足以迈动双腿的力量,挥舞匕首的力量,用嘴撕咬的力量......要什么样的力量才能让我——
这不是力量的问题,她焦虑地想着,这不是力量的问题,这不是,她们不是......
“同学,你身体不舒服吗?”
我抬头看向说话者,他看起来是驯化委员会(Tame committees),即使在说话的时候,他也没有看向我。这个时候我意识右手的指甲正陷在肉里。
我也许应该对他叹息,那种叹息将被献给一个不戴猪头面具的人。人们还是排列得那么整齐,在我的余光中,那个驯化委员会递归式地离开了礼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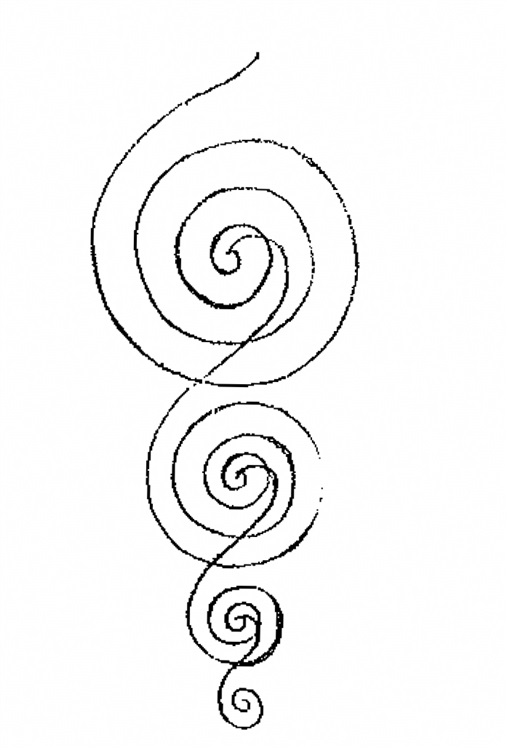
然后,我看见那个自称为我的兄弟的男人摆好架势,双眼中流出一种不可掩盖的需要,开始了。我躲过他粗糙的摆拳与鞭腿,他的拳面上裹着染血的绷带,掠过鼻尖的时候能隐约嗅到那种属于草原的独特腥香——他的妹妹是草药新娘,这就是在那个瞬间出现的想法。
攻击落空后,男人打了个踉跄,他的视角中闪过那些旋转着的炙热太阳,它们十亿年如一日地悬挂在草原干燥的天空之上,为由新牛(New Cattle)带领的羊群驱赶喜阴的毒虫。
我又避开了男人的一次扑击,在药物引起的周期性视错觉中,他的速度变得越来越慢,于是我走上前去,用拳头砸断了他的鼻梁。他的血液溅到皮肤上的时候,我看到了他为父亲送别时的那座悬崖,感受到铁锤落到绵软肉体上传来的异样手感,还有牙齿撕开老化的人类肌肉时的阻力。然后,我渐渐能够听到家人们的声音,他们用统一的节奏鸣叫着,不再是单子化的个体,而是一个巨大的无身体的喉咙,那喉咙振动人群组成的声带发出颤动不休的高亢歌声,从那种声音中逐渐生长出一座宫殿的轮廓。
我们撕咬在一起,我刻意迎上他拳头与爪子的轨迹,然后撕下他的耳朵,让彼此的鲜血更多地浸透对方。我听到他说金族的语言,那是一种方言化的草原语,它的音韵-结构就像克托尼俄斯的神殿一样复杂、神秘、宏伟,金族人从小就会说这种语言,这是一种多么幸福而令人羡慕的偶然。
我的兄弟脚步虚浮地后退着,抱在胸前的架势几乎失去形态,我冲向他的面门,他伸手想要架开我,奇怪的事情就这样发生了:他的双手从突然出现的酱红色虚空中穿过,那副曾与他分享血液的皮囊——“家人”的皮囊——蜕去了,从可怕的残余中伸出一只孩子的手,它奋力向前伸展,距离男人的身躯仅有半尺之遥,然后,从它的前端凭空生长出来自人类世的金属利爪,贯穿了男人的胸膛。
“交易。”喻蛹坐在奄奄一息的男人身上,轻轻按住随着呼吸起伏的匕首,男人散大的棕色瞳孔中生成了一张取消反射的脸。
“我们决定将您安插在总线部,总线部参事。”那张脸对少女说到。
少女俯下身去看它。
“柏拉图说过,政府应当由哲学家来领导,虽然我不能把政府交给你,但是可以把研究机构交付给你,从今天开始,你就是我们的副主管了。”
那个脸继续说。
“斯莱让克因蒙是谁?”少女问道。
一张自我取消的面孔从男人散大的瞳孔中站立起来,那是一张横亘于过去与未来中间闪烁的图像,那是玛利亚,祂的生成元在光与影的交错之处浸泡着,这张面孔已经在那些不可思议的外托邦中存在了百万年,上亿年,可为什么今天会如此频繁地出现呢?
“欢迎您,■■。”伴随着剧烈的视界闪烁。某种植物被迅速地抛出了它们的谱系学图谱,从女人的眼睛中再次生长而出。
“你是谁。”礼堂里空无一人,已经是傍晚,无色的太阳膨胀肮脏的暗色,投下的半阴影透过窗户落在礼堂各处,日常的物什在黄昏中沉默着,它们的阴影开始变换出真正异样的形体。我看见那个背影站在主席台中央。
他转过身来看我,那是一个男人。
我用匕首剖开男人停止起伏的胸口,从中取出了那颗被允诺的心脏。
......
咚咚
咚咚咚——你好,有人在吗?
这里是紧急联络电话,在发现红色时致电9339-
咚咚——咚咚咚
《雪花的暗示》 1993年 作者:
你好,是志愿者热线吗,我的院子里全都是兔子,它们一直往下掉,是的,我们已经
这是哪儿,一个穿着松垮人皮的人向我走来
没关系的,最后我们都得救了
把身体丢过栏杆,灯光在它湿漉漉的表面划过,它下坠着,仿佛要一直坠落下去
首先,这种场景已经出现过一次了
太阳用完了,上来吧,这里还有一个空位
少女走在古怪的森林中,一具身体从积雪的树冠间暴露出来,她的皮肤被红黑两色覆盖,皲裂的表面已经无法与肌肉区分
是的,你患上了轮回症,这会使得你的人际关系受到很大影响
如果它们有脚,就会像动物一样逃跑
看看这副面孔吧
它已经没了呼吸
需要这么做,你需要一颗心
确认返回,转动盾牌上的女人
我爱你别说笑了我愿意一直陪着你
那是老朋友,坐在失去饱和度的黄昏中,发条驱动的四肢咔嗒作响
红色
拨打紧急联络电话93
第一次红色出现在1997年,当时我们刚从球场上下来,它——那种红色——仅仅持续了一瞬间,也许是时间到了,我们
原来如此
阿姨你好,我是■■的同学,原来时间的限制并不重要,你的刑期是多少,一个天文单位,甚至是一个光年?
原来如此
原来如此
你还没见到
原来如此,我们被困住了,不是困在循环的时间中,时间的确在循环,但那只是一个表象——关于我们必须面对的真相的表象。他大声呼喊着,想要把这个绝对的发现告诉每一个人,但是没有人搭理他,他由激动到愤怒到歇斯底里,最后因脱水躺在地上动弹不得,原来如此,他现在想,现在我才明白了
“没有上帝,虽然我哭喊,我发现了他的影子,不能死去”
那个数字没有你想象的大,第十次播放时,一部分人开始声称自己体验到对当下场景强烈的既视感,我们发现第■■^■■^■■■■次播放的画面是 South Park 在1997年初次播出版本的选段,除了颗粒度较原版更高之外没有其他明显区别。进一步检索发现,首次空间异常发生在第■■^■■次播放中,此录像的行为在此后的迭代版本中出现了明显的概率越轨——最早在第■■^■■■■■次播放中,观察到了本体论性质的剧烈变化
你还没有见识到,垂死的少女突然扭过头看向我,她的肠子被扯到空中,人群爆发出一阵更巨大的欢呼
重复,你还没有见识到重复
然后,独白者在舞台上出现,一直到观众彻底散去也未离开,在此期间,舞台灯光曾数次变为红色
请拨打紧急电话933
他用二十年说完了这句话,最后一个词短促得如同叹息,然后他死了,连释然都来不及流露
我熬夜看了一个晚上的电视,其实到了后半夜,电视上已经没有任何节目,于是我就盯着那些雪花般的噪点看,直到一座走廊出现在画面中——天亮了,我应该去学校看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