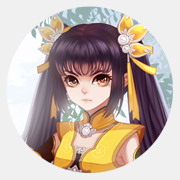却说鲁肃与楚旭、诸葛亮辞了刘备、刘琦,登舟望柴桑郡而来
三人在舟中交谈
鲁肃对诸葛亮道
“先生见孙将军,切不可实言曹操兵多将广……”
诸葛亮微微一笑
“不须子敬叮咛,亮自有对答之语。”
鲁肃见在诸葛亮这碰了壁,只好转向楚旭道
“先生口才,天下皆知,可结盟一事不比泼皮骂街,望先生切勿咄咄逼人,需就事论事,以理服人。”
楚旭露出人畜无害的笑容
“子敬勿忧,谁人不知我楚安济儒雅随和,风度翩翩?怎会做出骂街这等粗俗之事?等见了孙将军,我自有定夺。”
得到楚旭的口头保证,鲁肃也算是稍稍安了心
“如此最好。”
“噗……咳咳……”
一旁的诸葛亮强压上扬的嘴角,眼中满是笑意
三人一路侃侃而谈,等船到岸,鲁肃便请诸葛亮、楚旭于馆驿中暂歇,先独自前去汇报孙权
时孙权正聚文武于堂上议事,下人来报
“报将军,子敬先生已回矣。正在堂外等候。”
孙权急召鲁肃上前,迫切问道
“子敬往江夏,探虚实如何?曹军兵马共有多少?”
鲁肃根本没从刘备那问出什么有用的情报,但又不敢瞎编,只好擦了擦额头虚汗,打马虎眼道
“肃已知其略,稍后便为主公详解。”
孙权点点头,随手拿起桌上一篇檄文,对鲁肃道
“曹操昨日遣使至此,将此檄文交于我,我不知是接受还是拒绝,现今正召集众位商议。”
鲁肃接过檄文细细观看
其上书曰:
『孤近承帝命,奉词伐罪。旄麾南指,刘琮束手;荆襄之民,望风归顺。今统雄兵百万,上将千员,欲与将军会猎于江夏,共伐刘备,同分土地,永结盟好。幸勿观望,速赐回音。』
鲁肃一顿,思索道
“这……这……”
“以老夫观之……”
这时,有一老者站了出来,朝孙权行了一礼
“现如今,曹操拥百万之众,假借天子之名,以征四方,所向披靡。而主公雄踞江东,赖以拒操者,长江也。今操既得荆州,长江天险,其也拥之,已势不可敌。以老夫之计,不如纳降,可得永世长久。”
孙权摸了摸下巴
“张子布所言……诸位意向如何?”
众谋士左顾右盼,通了眼色后,齐声道
“子布之言,正合天意。”
孙权将他们的小动作看在眼里,沉吟不语
张昭又行礼道
“主公不必多疑。如降操,则东吴民安,江南六郡可保矣。事不宜迟,迟则生变。望主公采纳!”
孙权依旧沉默,眼神闪烁,不知道在想什么
“不可!”
这时,鲁肃开口了
孙权眼前一亮,急问鲁肃道
“子敬有何高见?”
鲁肃扫视众人一眼,道
“不敢妄称高见,只是肃有一言,望主公听之。”
他对孙权道
“就在前几日,刘备帐下谋士,于长坂坡一战时,为曹操掳走,然,其在曹营中,四面受敌,仍宁死不降,列举刘备之往事,骂得程昱程仲德吐血昏倒。”
孙权不解道
“子敬,你想说什么?”
鲁肃恨铁不成钢道
“昔日楚安济于曹营中尚能坚守本心,不为曹贼同流合污;而诸位,却在曹贼还未攻来,不过发来檄文之时,便欲投降,将江南六郡拱手相送,以求荣华富贵,岂不为外人所笑?九泉之下,何见伯符将军?怎见乌桓候?”
说罢,他对孙权下拜道
“肃宁死不降,投降一事,还往将军三思!万不可将父兄基业送于曹贼!”
“鲁子敬,你!”
张昭还想说些什么,却被孙权制止了
“好了,鲁子敬所言也不无道理,此事容我三思,诸位皆退下吧。”
众人皆告退,惟鲁肃仍在原地
不多时,孙权欲去更衣,鲁肃紧跟其后
孙权知晓鲁肃心意,便对鲁肃道
“子敬欲如何?”
鲁肃道
“方才众人所言,深误主公。其余人皆可降曹操,惟将军不可降曹操!”
孙权一愣,不解道
“子敬何出此言?”
鲁肃语重心长道
“如我等降操,无有后顾之忧,事后仍可得一官职,最次不过告老还乡,有家族接待,不失荣华富贵;可若主公降操,又会如何?位不过封侯,车不过一乘,骑不过一匹,从不过数人,曹操又怎会赐给主公封地,让主公自在的称霸一方呢?主公岂不闻刘景升之子刘琮身死之事?此便是主公的前车之鉴啊!”
孙权沉默了
鲁肃趁热打铁,继续道
“众人之意,各自为己,不可听也。主公宜早定大计!”
孙权沉吟片刻,仰起头四十五度角仰望天空,长叹一声道
“诸人议论,令我大失所望。而子敬开说大计,正与我意见相同。此天赐子敬于我也!但曹操新得袁绍之众,近又得荆州之兵,恐势大难以抵敌……”
鲁肃生怕孙权真的投降曹操,连忙道
“肃至江夏,引诸葛瑾之弟诸葛亮与其好友楚旭在此,主公可问之,便知虚实。”
孙权一惊
“楚安济在此乎?”
鲁肃点了点头
“二人现在馆驿中安歇。”
孙权颔首道
“不瞒子敬,先前周公瑾与我谈过楚安济,他称其为当世奇才,子敬以为如何?”
鲁肃道
“公瑾所言非虚,我观楚安济仪表堂堂,风度翩翩,举手投足之间有萧何、张良之范。”
孙权颇感慨道
“可惜今日天晚,且未相见。来日聚文武于帐下,先教其见我江东英俊,然后升堂议事。”